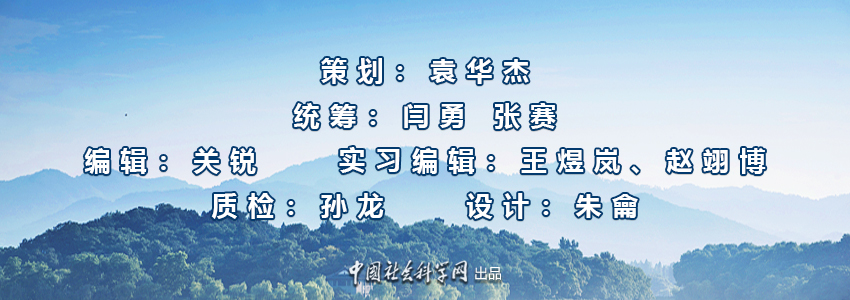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网:推进两岸现当代文学研究交流——第二届琦君研究高峰论坛在温州召开
作者: 来源:金沙集团1862cc 时间:2022-06-01 阅读次数:次

5月21日,第二届琦君研究高峰论坛在温州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共温州市瓯海区委、瓯海区人民政府主办,瓯海区委宣传部、瓯海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瓯海区文联、金沙集团1862cc、《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杂志社等单位联合承办,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琦君研究、琦君作品和文学教育、琦君作品文本细读、琦君与故乡等议题分享了研究成果,展开了交流讨论。

琦君女士一生默默耕耘,作为享誉海峡两岸的文化名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作品蕴含着真诚浑厚的情感,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中国风味的散文家,影响着海内外华人和每一位读者。几十年后的今天,琦君文化焕发勃勃生机,已成为瓯海文化发展中的乡愁文化新名片。

2018年的11月24日,首届琦君研究高峰论坛在瓯海区行政中心隆重启幕,15位来自海峡两岸及日本的琦君研究学者和来自温州本土的琦君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共100余人参加了活动。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相关论文收集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琦君:2018在瓯海》一书里。时隔三年,第二届琦君研究高峰论坛举办,这让我对本次论坛充满了期待。

琦君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也推动其文字更具有文学的温度,这也是其作品最珍贵的地方所在。琦君的文学作品对于市场的适应性与流通度都是首屈一指,究其原因在于,对于大千世界的阐述与对客观世界的刻画,都让人身临其境,并形成了所谓的“情境之美”,这是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目前关于琦君研究的论题涉及琦君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文本解读、创作主题、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审美风格等方面,也涉及琦君创作的各种文体,研究相当充分。尤其是怀乡书写和亲情书写的作品,更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琦君对故土故事的讲述,大致都停留在爱与美交织的童话传奇中,但就目前的研究资料汇编和整理中发现琦君作品中,对于故土的书写与阐述存在记忆编码的虚构成分。关于此问题,台湾地区的学者在研究琦君作品时发现,她的文字克制情感,以及通过分析其童年经历来建构深层次的心理感受。此篇文章意在剖析琦君作品中对于故土故事的记忆编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对中华文学史的研究发现,学者琦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可撼动。其文字既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新文化下的滋养,两种意蕴在琦君的文学作品中交织呼应,自成一派。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琦君文学创作中的哲学层面,对琦君身处个体生命的极端低谷时生存哲学的生成进行研究,对于“琦君之爱”的生成源流、生成时机、引领人物深入剖析。

不同于冰心和张爱玲,琦君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质,风格清晰,换言之,琦君的文体话语有其典型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悲悯上,是哀伤而同情的。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感同身受,读者和琦君一道,生成一种基于人间苦难的慈悲情怀,继之以人类的普遍性同情,而这同情是没有怨恨的,甚至连可怜之气都没有,是对人间苦难和处于苦难中人的不轻视、不蔑视。琦君笔触清澈,她对笔下的世界和这世界里的人给予的批评比较少,讽刺就更少了,其文字是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爱,这种爱也弥漫至人性的最广阔处,让一位女性作家变得温柔而有力量。

琦君的一生折射出时代的巨变,琦君研究也相应地体现出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批评研究的影响。琦君已然成为一个符号,或被纳入第一代迁台女作家群的论述框架,或放进主题研究的热浪中被层层剖析,或成为比较研究中用来验证结论的一个具体例证,或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实现”女性的蜕变,或在离散叙事中抒解乡愁……琦君研究热切地探索琦君在台湾文学史中的独特性,而研究本身同时也呈现出不同时期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时代特征。

琦君的故事,反应的是她少年时代对于家国的记忆和经历,淅淅沥沥的雨水也反映了从前时代中女性共同的悲剧。琦君笔下饱含着对故乡深厚的眷恋,这是我们常见的论题。同时我提出了女子是否应该受教育的观点,从而观察琦君文章中有没有一部分女性主义意识的萌发。琦君说她所塑造的秀芬其实是很多旧时代苦命女子的缩影,所以她非常狠心地让这个人物担负了更多的苦难。

从琦君的文学创作流程来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主要散文与小说的创作,所取的题材基本上是远离大陆到台湾的人对故乡的向往思念。琦君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小说是《钱塘江畔》《完整的爱》《梅花的踪迹》等,从这些小说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琦君对爱情与家庭的社会伦理观念,表现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所具有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金盒子》《下雨天,真好》《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筒》等文章中,可以读到琦君深沉的恋乡思亲的乡愁情感。

琦君旅居美国二十余年,既是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入参与者,又是清醒的旁观者和深刻的审视者。她书写美国,就是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诉诸笔端、构建美国形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她的多重叙事角色共同作用,不仅使散文明显呈现出叙述中夹杂议论的特点,而且构建出了立体多维的美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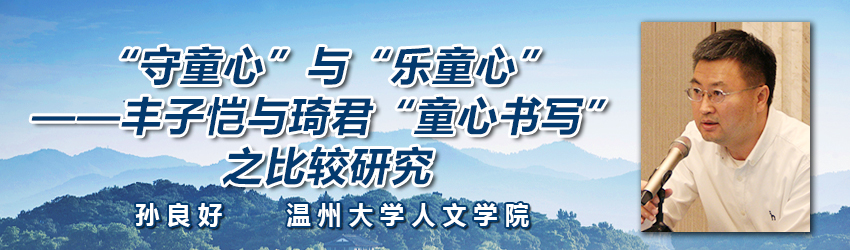
丰子恺作为五四时期发现儿童的代表作家,高举“以儿童为本位”的旗帜为儿童代言和写作,他对孩子的喜爱可以用痴迷来形容。琦君比丰子恺小近20岁,但一样能成为儿童的朋友,这是因为两位作家都有一颗童心。但是,他们的童心又因个人的成长经历与阅历、个人的性格气质和外界的影响,闪耀着不同的光芒,在照亮各自生命之旅的同时照亮一代代读者。在“童心书写”的过程中,琦君在过去的童年时光中汲取了童心的力量,较丰子恺更能用纯净的童心体验现实,积极看取人生。丰子恺和琦君都明白童心可贵,前者选择守护童心,后者选择与读者一起分享童心之乐。

从地方路径来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大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地方”,一是故国的,一是他乡的,这两种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华文作家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于琦君而言,长于温州瓯海,徙居于台湾、美国,江南形胜、永嘉文脉濡养了她的温婉和坚毅。虽然在她的创作中既有台湾生活,也有异国经验,但写得最好最多的,还是那些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怀乡思亲类作品,家乡味、怀乡愁永远是她作品的思想内核和情感基质。

琦君接受了中西优秀文学传统的滋养,语言纯粹、干净,适合于青少年阅读。琦君的儿童文学书写,基于回忆,童心不泯,至情至纯,过滤杂质,始终注意教化功能。她常常以儿童的视角观察,或者以母亲的身份忆述,描绘善良、美好,规避展露人性的恶,在文中有意识地强调道德修养方面的因素。琦君纯粹、干净、规范、平易而又优美的语言,赋予其散文以儿童文学性,增强了琦君儿童文学的传播热度。

琦君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平民化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审视社会生活的窗口,即琦君通过自己的讲述,既展现了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又为普通市民在各个方面烙上了异于过往的“时代印记”,而这更为当代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航标指引。

当我们从文化哲学视域观照琦君的文学创作,便会发现其中贯穿着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哲思性认同,她把文化、人、社会、民族等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同时又是生命链上不可缺失的环节,互生互息,不可分割。

自《烟愁》以后,琦君大部分的散文作品,均维持着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温柔敦厚”风格,她尽量将“不堪的”“残酷的”内容刻意忽略抹去,只将那些“美好的”“善良的”部分留下。而正是从《烟愁》开始,琦君才真正确立了其独有的“温柔敦厚”式写作策略,并且将之贯彻至日后的散文书写当中。

琦君的长篇小说《橘子红了》,不仅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还形构了独特的“家宅”形象。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家宅是我们在世界的一角。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家宅在小说中就是凝聚了琦君复杂情感的独特存在。在小说中有大量的与家宅相关的场所描写,如院子里——“庭院深深,人影寂寂。久远的容家老宅在夜色里显得神秘诡异。”院门口——“容家大宅没有清静多久,雕花铁门又被推开,传来嗒嗒的高跟鞋声”等等。

正是时间线索与片断式感觉印象呈现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故乡与童年》的诗情画意拥有了诗意的结构特征。而我们就在琦君娓娓道来的诗情画意里,感受着蕴含在“儿时情景,历历似画”背后水乡人勤劳朴实的生之趣味,以及乡邻之间和美良善的人文情怀。